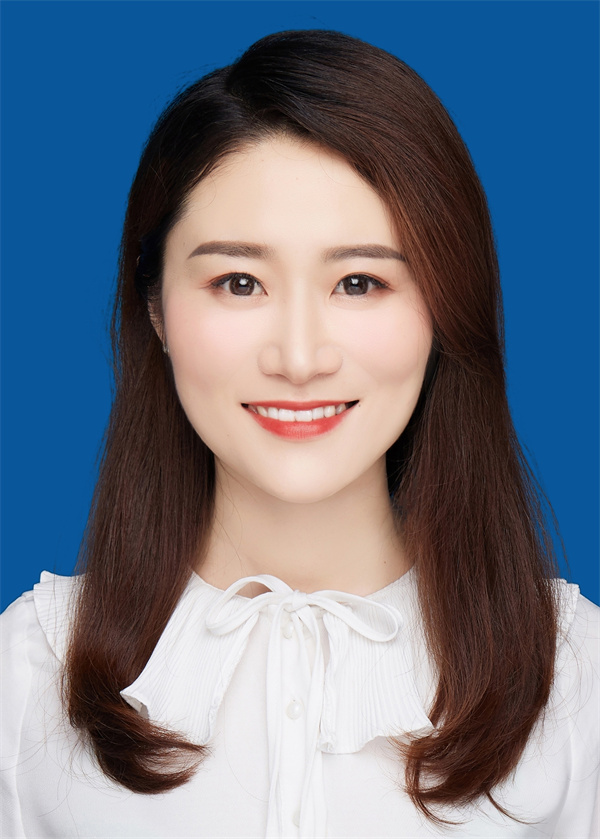编者按:
2018年12月8日下午,南徽读书会第15期特别版“南徽艺术沙龙 - 夏汉诗歌对话与分享”活动在南徽书屋举行,活动邀请诗人、批评家夏汉作为分享嘉宾,90后作家张亚主持,本期主题为 “诗歌创作与心灵疗愈 - 90后诗歌情绪与自我表达”。
同时,这也是《南徽对话》栏目第1期访谈实录内容,日后“南徽艺术沙龙”将独立板块,与《南徽对话》栏目同步进行,会邀请语言艺术、表演艺术、造型艺术、综合艺术名家在南徽书屋举办活动,并进行“南徽”全媒体报道,敬请关注。

张 亚:
夏汉老师是河南夏邑人。多年来,写诗,兼事诗歌批评。累计有诗五百余首,批评文稿七十余万字,诗文先后发表于《诗探索》《诗刊》《西部》《安徽文学》《奔流》《飞地》《汉诗》《山花》《江南》《大诗论》《读诗》《文汇报》《光明日报》等国内报刊及多种诗歌选本。出版诗集《冬日的恩典》(黄河出版传媒集团/阳光出版社,2014年)、《街头的证词》(南方出版社,2017年),批评文集《河南先锋诗歌论》(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语象的狂欢》(南方出版社,2017年)。现兼任河南师范大学华语诗歌研究中心(社会事务)执行主任。今天的沙龙主题为:诗歌创作与心灵疗愈——90后诗歌情绪与自我表达。现在,请夏汉老师就此话题展开对话。
夏 汉:
先谈一个题外话:2015年初,决定做一个90后专题。这是缘于近年接触了90后诗人以后,发现这个群体中有的已经写得很好了,比如当时在上海读书的秦三澍,四川大学的莱明,西南交大的王江平、陈玉伦,北京的李婉、苏笑嫣,还有河南的狂童、高爽,贵州的蒋在等等。那时候看到他们的文本已经都很有完成度了,有些已经可以达到谈论诗艺的程度。当然,一些优秀的90后诗人的写作在20多岁的时候,尽管已经初步显露出来,但很难进入批评视野, 这都缘于批评体制的局限性。事实上,海子死的时候才25岁。在西方,天才诗人兰波16岁就写出著名的诗篇《奥菲莉亚》,翌年便以通灵者自诩,求索于潜意识和幻想的自由诗风,《元音》和《醉舟》成为象征派诗歌的代表作,完成《地狱一季》与《彩图集》而放弃写作才17岁。包括现代主义创始人波德莱尔, 22岁开始就陆续创作后来收入《恶之花》的诗歌。总之,他们在写作的时候是20-28之间。现在的90后诗人最大的已经28岁,除了钱文亮、杨克等人写过单篇文章,这个群体并没有进入研究与批评的视野,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故此, 我想开始进入这个课题。当年写了约5万字的文章,后来陆续发表在国内几个刊物上。尽管有不少批评界的朋友担心,我还是坚持把这个课题做下去,我相信对于当下的年轻诗人会有用处,至少我可以做到发现与梳理。我设计了一套90后诗人答卷,意在了解90后写作者的实际状况,以利于做进一步研究。
当我看到这个话题以后,就在考虑,这其实是指心灵和写作的关系。这是一个我们目前所普遍关注的话题,关乎一个人的心灵真实状况。我最近在读一本书,叫《浪漫主义的根源》,以赛亚·伯林在这本书里有一个说法,他说,人类作为灵魂的拥有者,也就拥有了精神需求,那么,在追逐自由的天性里,就“具有非理性的因素,存在着潜意识的深层,他们内心涌动着各种黑暗的东西”,同时,他们蔑视作为理性的僵化的规则,期待着“让精神融入伟大的狂喜之中”的幻觉,自然也会涵括精神深处的痛苦。叔本华则说,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这也正是卢梭所谓的: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总而言之,这些经典说法给我们传达了一个意思,人生难免于痛苦与不圆满。我们在这样的哲学与思想背景下,观察90后这个生命群体,我觉得最明显的有两种情绪,一是比较焦躁,这种焦躁的情绪有时候还可能来自于对这个时代的焦虑与不妥协;另外一个就是迷茫,就是说对这个社会和自己的生活不知道怎么办? 这样,就需要寻找一个出口。寻找好了就可以转化心灵上的负面资产,不至于让一个人一生都居于痛苦乃至于绝望之中。 那么,对于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学,或许你找到了诗歌这个出口,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我觉得这个出口找到了,就会拯救一个人负面的与黑暗的、迷惘与矛盾的心绪,让你有一种好的转化与宣泄。我们知道余秀华就为自己寻找到一个诗歌的出口,从生存的意义上,她选择对了。还有一位你们同龄的诗人,常州的许天伦,从小患有更严重的脑残,四肢瘫痪,十个指头只有一个可以敲击电脑键盘,他凭着坚强的毅力,在电脑上学会识字与拼音,读诗与写作。目前的诗歌完成度很高。现在已经成为国内著名的诗人,可以说是诗歌拯救了他的苦难与绝望,我已经为他写了一篇专论,等待杂志发表。
我觉得诗歌有两个功能, 首先是审美。每当你进入诗歌的时候,诗歌的审美创造可以转化你的不良情绪——绝望、迷惘与焦躁等等。这个实际上是把所有负面的感受:黑暗的、绝望的都转化成一种审美的时候,那么负面的东西就有了他的价值。当然,对丑恶的东西的转化也属于审美范畴。其次,诗歌是语言的最高形式,我们所有的情绪,都来自于没有语言的化解,大家都知道哲学的很多的东西——所谈到的对世界的认识,都来自于这种语言的赠与,它是利用语言转化了我们的情绪,那么这种赠与就让我们的心灵有所变化。就是说能够进入语言的时候,进入像今天这些诗歌文本的时候,这就是语言的呈现。正是由于审美和语言,让我们的情绪转化或者心灵转化的时候,就进入了今天的副题:治疗。这也应验了费尔南多·佩索阿所说的:真实人生是不完满的,艺术是对于人生的主体的完善。
我觉得还要谈的话,你们在大学里边可以谈很长时间。老师备课可以谈一周,分成几个话题,谈这种灵魂转化出口、宣泄,以及语言审美。其实我更感兴趣的倒不是这个话题,而是这个话题之后,进入语言之后我们的写作,这一点才是我们今天到这里来的最感兴趣的话题:从情绪的转化,到诗歌文本的完成,或者说怎样让诗歌写得更好,怎样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 90后诗人(特别是95后)现在在社会上,经常被诟病,或者不被承认,那么为了让他们能够承认,能够在未来进入学术阐释,我们更重要的是怎样把诗写好,怎样做一个优秀的诗人, 所以这个话题之后,我可以听你们最愿意提的问题,我尽最大可能跟大家去交流, 大家可以随意说,跟诗歌有关的没有关的。只要是提出了问题,我都会尽力回答,我也想知道你们在想什么。说不定就会把你们的一些问题,纳入我的写作思考。
张 亚:
我先提一个。我的一个感觉就是,像前些年大学那会儿,我们那一批人写的诗歌都很张扬,情绪的表达也是比较重的,但是经过工作这几年之后,反而会沉淀下来,更不愿意去给别人交流诗歌,和普通的一些朋友,我就会觉得没有太多可聊,但是大家在一起去聊诗歌的时候,又觉得很羞于说我之前写过什么,或者怎么样,更愿意的是闲暇之余去默默的写,那您觉得像九零初的到了我们这个年龄,这一批的都是从原来的张扬到后来可能窝在办公室或者窝在一个角落默默的去写,但是内心确实很开心的,我会觉得从以前的张扬到现在我的一个沉淀、积累,那是我内心的一个安慰,但是很多人都会觉得你是不是不写了,那您怎样看待这种心理的变化?
夏 汉:
我觉得这种状况很好。其实,从开始写作的时候很兴奋,找同学或者朋友在微信群里或通过其他方式去聊,那是一种很兴奋很幸福的情状。到写了一个阶段以后,慢慢的沉静下来,反而有利于诗的完成,或者一个优秀诗人的完成。每个具体写作,比如一首诗,你也不知道什么时间到,但是到来的时候,你即便在火车上,在航班上,你只要有可能,都会去写作。什么情况你都可以不予顾及。在闹市你照样很安静,把你这首诗完成。 说白了,按照策兰的美学追求,诗歌是一种进入语言的陌生地带,是一种沉默的、不可言说的言说。当一个诗人能够写到这种状况的时候,当语言能够进入那种不可言说的言说,一个陌生地带的探索的时候,那么所有的张扬和行动这些外在的东西跟诗歌几乎都是没有关系的。那么你这种安静的沉默的写作,正好符合一种你当下的此时此刻的一种写作的最佳的心理状态。我觉得这个很好,要坚持下去。
张 亚:
以前写作的时候是只能静下心来,没有外在骚扰的时候才能写东西。但是我现在发现,写作已经有了变化。我前段时间去香港,回来的时候,很晚了,我在开车的路上看到下雨了,有几个人在骑着电动车淋着雨,在那里穿梭,突然心里就有种感觉,我回去后就写了一首。这么多年的一个变化是我觉得诗歌更多的是自己,就是内心很自然的一种表达,不像最开始的时候是为了文学理想,为了某个想法才去做的,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更多的是内心最真实的表达,那种很简单的一种表达。
夏 汉:
我觉得这种状态挺好的。像我们这个年龄,曾经是一个很大的写作群体,现在很多都已经趋于那种安静的沉默的个体性行动,要不发表,很少有人知道他在写作。但凡还在坚持写作的人,他就在写那种很内在的属于个人真实的东西,而这种写作是很有价值的,可以说这样的写作才更趋近于写作的内在与本质。
李三金:
诗歌到底有什么作用,怎么影响着一代一代人,然后影响到90后这一代。我也是90后,上大学都在写,但之后可能就不会写诗。可能在生活的某个情景中,我还会用到。比如说我会“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某特定情景,我会引这首诗,我觉得对我确实是有情感治愈的,或者说能适合那个情感情境的作用。但是对更多的人来讲,或者说更多的情景下,尤其是现代诗歌,对我们这些人是否还有情感治愈的作用,它的这些作用是否已经被其他东西所替代了?比如说一些歌曲。90后有这样那样的心理问题,但是诗歌好像没有被用来去治愈这些。
夏 汉:
其实这个话题很大,我与朋友交流的时候,也常常会谈到这个话题。这位同学说到唱歌,我觉得也是好事,生活与学习、工作都很累,跑到歌厅唱唱歌,或者自己收听,我觉得很好,每个人都为自己寻找一个出口,排遣自己不良的情绪,寻找一个宣泄,从社会学的角度,是成立的。而说到诗歌到底对我们,对普通的老百姓有什么用?从道理上讲,我觉得,诗歌有用和很多人觉得没有用都不是诗歌本身的问题。如果一首诗成立,就一定会有作用。记得阿米亥在《诗人教育》里就说过:它是一种抵抗绝望的阻挠因素。如果一首新诗能够成立的时候,它的完成度达到了而没有发生作用,很大的可能是这首诗还没遇到知音,就像希梅内斯所说的诗歌是献给无限的少数人的,一首诗的知音原本就少。诗歌没有对我们发生作用,是因为很多的诗歌没有被发现。我们身边充满了娱乐,以至于像尼尔 ·波兹曼说的娱乐至死,很多人并没有去关注诗歌。就当代汉语诗歌而言,德国汉学家顾彬有个说法:1979年以后,中国的诗歌肯定没有问题,80年代的中国诗人可以和世界上重要的诗人相比较。80年代,中国文学的成就主要在诗歌,而不是小说。他这个说法意味着什么?显然是指优秀诗人和优秀诗歌的数量与质量。那么,为什么没被发现?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诗歌的普及教育不力和我们整个的时代对于诗歌的疏离与慢待,以至于让诗歌远离了我们的生活。诗歌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很高贵的东西,而我们身边居然没有诗歌,这是很悖谬的情形。现在,我愿意以一位诗歌同道所说的话结束这个话题:可以肯定地回答,现代诗歌有情感治愈的作用,它不是歌曲等其它东西所能替代的,即便有时候看起来替代了一部分。比如歌曲,能慰藉情感,这是经验证实了的。但那还是属于浅层的一种情感的分散、发泄或者转移。之所以大家认为诗歌的情感治愈作用不够明显或者显而易见被歌曲“替代”了,那也是因为歌曲易于在大众之中流行与传播,对文化、审美等的要求不高。而诗歌则显然对受众的文化素养要求更高,诗歌是为有准备的人预备的精神大餐。
向海洋:
咱们谈口语诗的时候, 刚才夏汉老师提了一个点,可否就这个话题多谈谈?
夏 汉:
诗是文学中最高的一个语言形态。 刚才有同学谈到的梨花体、废话体,我觉得到现在为止,任何一个大学的文学院都没有去研究它们,这些东西是不会进入一种真正严肃的文学门类的。而口语诗并非不好,我多次说过,能够写口语诗的人都是很聪明的,因为口语诗并不好写:那种看似很简单的叙述其实有着很高的功力,或者说,好的口语诗一定很耐读。记得奚密说过这样的话,好诗在于它是否能经得起一再的阅读和诠释。可能一首诗看起来一点也不复杂,它没有典故,文字是大白话,但是它非常耐读,因为它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表达前人已经说了一万遍的感情或思想。这在我看来就是成功的一首诗。我同意现代主义的中心原则,那就是创新。如果一首诗只是重复别人,毫无创意,就算不上好诗。她还以美国诗人威廉斯为例,说:“他的诗通常又短又简单,没有炫目的修辞。但是你会想一读再读,因为里面有些东西触动着你。作为读者,我总是试图去接近诗的核心。”好诗的确如此。事实上,当代口语诗就来自于美国口语诗的影响。但问题是,在当下很多人写成了口水,就已经不是诗了。 当一首诗失去了诗歌的难度的时候,那么这首诗就值得怀疑了。诗本身是个很严肃的东西,如果都搞成通俗文学了,我觉得写诗的人其实就没意思了。据我了解的,现在民间也好,大学也好,很严肃地写诗的人还真的不少,包括你们90后诗人群体。
张 亚:
我是这么认为的,其实我觉得我也算是一个例子。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像我们去河南参加90后作家联谊会的时候,像有人讲的那样,九零初那一阶段的人,很多是写诗的,当时我还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在全国还算比较有名气,大概做了四年左右,然后我是属于那种突然消失了,是因为我出来工作、创业了。但是这么多年我还在写,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还在私下里写,只不过很少投稿发表,不像前几年的时候,为了文学很张扬。学生时代,我更多的是花的父母的钱,这几年我认为的是: 先生存,生存是第一位的。诗歌对于我来说,不是说一定要出书,或者是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更多的是我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宣泄,一个窗口。每个人宣泄的窗口不一样,有些人就是去KTV,或者是哪个地方去旅游,还有些喜欢书法,写个书法,他心情就好了。对于我来说,能静下心来写诗,我觉得是个宣泄。在我创业阶段,压力很大,这是我宣泄的一种方式和一个窗口。生存是第一位的,我始终是这么认为。我创业这几年得到了我想要的生活,实现了我的财务自由,我各种条件都达到了,那现在我又反过来,就像去年一样, 我为什么开了这个书店?就是因为我挣到钱了。我创业才用不到两年的时间,一年多的时间,我5万块钱创业,3万块钱是借的。很快的时间我买车了,买房了。而我突然觉得心空了,我始终会觉得少点啥,当时我做这个店的时候,我又静下心来去写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又是一种回归,包括现在很多的杂志,报纸开始又找我约稿,他们约我还是诗歌,在他们的眼里可能我还是当初从诗歌走出来的这个人。第二个是我觉得你自己最舒服的那种状态,一定要找到你自己最舒服的,不要说我为了写诗歌,我朋友也不交了,什么也没弄了。诗歌不是一种痛苦的存在,如果说你在痛苦中一直在创作诗歌,从我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即使你创作出来的诗歌,可能也不是很好。我觉得我现在挺好的,我能够写写诗,我有自己的生活,我觉得我现在是很享受的一种状态。开这个书店我觉得是个功德。 诗歌这个东西,是小众,是希梅内斯讲的所谓的献给少数人。那么诗歌的用处在哪里?我觉得诗歌是很奢侈的东西,是个很高贵的东西。
夏 汉:
我觉得诗歌这个东西正是因为它高贵和奢侈,所以当你进入以后,你写作一段以后,你的内心,对它才会念念不忘。如果你的语言天分还能跟上来,能写几首诗的时候,你就可以坚持下去。 我给大家谈一谈我的一些经历。我是60年出生,15岁喜欢诗歌,原因可能是当时我的语文程度好一点,而我的班主任都是教语文的,恰恰我初中、高中的时候,我的老师也喜欢写诗,他们给我拿了很多的诗集看,然后我就学着写。我是农校毕业。78年应届高中考一个中专。然后就到农村。工作以后,我是99年做的镇长,39岁。在做镇长之前,做了两年的社会学研读,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的所长,姓陆,在访谈中说得非常明白,一个社会学家在基层一生能做一个案例,就了不得。他这句话对我打击很大,觉得一生做一个案例太没意思。而我觉得做镇长也没意思。因为早年的文学理想是想写长篇小说。作镇长没时间,但可以写诗。我完全靠自己学习学来的。能够学到今天这个水平,我不说我怎么聪明,只能说我喜欢诗歌,我做了我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情,我已经58岁的时候,能够在你们面前,在你们大学生面前,一个中专生还能坐到这个位置上,给大家平起平坐的讲话,我就感到很欣慰。那么就是我自己付出以后,换得今天的一个尊严,我还是感谢诗歌。所以诗歌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值得去做。当你认为能释放你的不良情绪的时候,当你觉得值得做的时候,当你认为这是你生命中不可割舍的时候,你不妨就做个诗人。
张 亚:
今天很感谢夏汉老师,他正好从郑州来海南这边出差,才很有幸邀请到他,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请教的机会。三亚这个地方,我也认识一帮喜欢诗歌的同学和朋友,我们也都有群,夏汉老师现在在研究90后诗歌,你们如果有作品的话可以发给夏汉老师。而且现在他在做一个问卷调查,大家可以去填写一下。我们以后也可以经常的做一些交流,因为夏汉老师可能会经常在海南。我们以后也会有不同主题形式的交流和分享。最后,我这一块也有做出版,如果你们有一些关于出书,或者你们自己的一些好的想法,都可以随时找我来交流。这个场地,如果需要举办读书类的活动,我可以无条件的去支持。(完)
 会员投稿
会员投稿 手机版
手机版 |
文艺频道
|
文艺频道